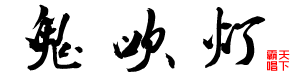过去?我望了望那两丈余宽的河道,顿时又发了愁。办法不是没有,丢根绳子过去晃两圈绕住一个固定物,再固定好绳子爬过去就行了,一般都是这么个做法。
可这说起来挺容易,干起来还真是个技术活,对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想套住个东西是不容易的,我们的装备大多都丢在蛇盘河里了,没有冷烟火也没有照明弹,完全靠运气绝对有点难度,毕竟运气这东西有时候是很不靠谱的。
绳索我们有,长度也足够,鹰戈用特殊的方法打了一个活结,将一个石俑的脑袋捆在里面,一拉紧再打个死结,石俑的头便被牢牢捆在里面。
这里的黑暗实在骇人,就好像能吸光一般,我们的手电光居然连七八米外的对岸都没法照清。其实我也很清楚,我们的光源经过长时间使用,明显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光线明显黯淡了许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
鹰戈还是能想到办法,他点着了一根火把,抡起胳膊甩到了对岸,一晃而过的火光照出了对岸一根巨大的立柱的轮廓。于是他再点着了一根,嘱咐我照他的样子甩过去,朝着立柱的方向,他同时把绳索甩过去绕住那立柱。
我身手不济,第一次居然没甩到位,再点着根火把试了一次,鹰戈总算找到了准头,系着石俑头的绳索在立柱上绕了几圈,牢牢地固定住了。
爬绳索我们不是第一次,还算是有点经验,这次的压力要小一点,最起码底下不过是河水,不是能把人摔得脑浆迸裂的石头地面,很快地,几人都顺着绳索攀了过去。
我们刚坐定准备喘口气,鹰戈突然又做了让我们隐蔽的手势,望着前方伸手就从背上摸枪。
我心道怎么了,遂一边作戒备状一边朝他望的方向望去,正如龙少所说,石俑阵并没有从这里断开,而是一直延续,朦朦胧胧间,我看到不远处的一座石礅旁,似乎蹲着一个人!
这里有很多石俑,我之所以觉得那是个人而不是石俑,是因为那东西的姿势很奇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借着石礅为掩体,举枪在向我们瞄准。
我们一直都高度怀疑这里有其他的队伍,不得不加强戒备心理,所以鹰戈的举动绝不是草木皆兵。想到这我倒有些担心起来,就凭咱们这人马,一个退伍大兵带着几个文化流氓,真干起来指定只有挨宰的份。
就这样对峙了一会儿,未见对方有任何异常,要真是个活人,是敌是友也得吭个气吧,难不成是之前遇到的那种粽子?
鹰戈随手捡起块石头,照着那玩意儿就丢过去,一看还没反应,这才确信没有危险,他猫着腰小心地贴了上去。随后他朝我们示意已经没事了,我们这才跟着凑上去。
这的确是一个人,浑身着迷彩服,从装备上就能看出他的专业性。这人趴在一块石礅上,双手紧握一支M16,仰面朝上,嘴巴张得老大,眼睛也上翻,死状十分恐怖。
三炮觉得恶心,朝着他的脑袋一脚将他踹倒,他脑袋一扭便倒到了地上,双手仍然牢牢地握着武器,眼珠子还瞅着上方,看那模样,之前显然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搏斗。
“这是什么人,怎么死在这儿了?”风师爷自言自语地道,一边说一边往四周看。他这么一说我当下也缺乏安全感了,随着他的目光四处扫视,很快就发现四周的乱石堆里居然还有几具尸体。
尸体有五六具,四周的石俑散落倒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那些尸体躺在石俑之间,黑乎乎的环境中看起来与石俑无异,四周还散落着一些子弹壳,正如之前猜测的,这里似乎还曾进行过混战。
我自然知道这肯定不是两队人在火拼,只是这些人到底在和什么东西搏斗,为什么他们如此荷枪实弹的都遭到惨败?虽然他们的失败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但此刻看到竞争对手的惨状,我们都丝毫没有庆贺的意思,反而是四周无边的黑暗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鹰戈来到一具尸体前,小心地检查了下他的脖子和头部,并没有发现什么致命的伤口,接着他用匕首挑断他的衣领扣子,一把扯开他的上衣,眼前的一幕险些让我呕吐出来。
这人的整个胸口、腹部、后背上全是破开的血洞,就像被人丧心病狂地用匕首捅了几百刀一般,再一检查,发现脑袋上也有很多。那些洞口大小基本相同,流血却很少,看起来就像是全身长了很多眼睛一样,恶心得要命。
鹰戈检查了下其他几具尸体,基本都无异,有几具尸体的脸上都布满了血洞,连眼珠子也没了,整张脸完全破了相。
眼前的一幕那叫一个惨不忍睹,我们不是没见过死人,只不过那些都是多则成百上千年、少则数十年、即将化为尘土的躯壳,这样新鲜血腥的还是第一次见,那血腥气止不住地涌进鼻孔,让人止不住就呕吐起来。
鹰戈道:“都没救了,他们身上还有不少东西,我们拣一些用得上的吧!”
这话倒没人不赞同,我们当下缺的就是装备,这帮人的东西与其在这里丢着,不如发挥些余热,这样一想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
我们找到五四式手枪两支,M16三支,还有两个大包,里面装着冷烟火、登山绳、狼眼手电、弹夹、蓄电池、照明弹、几捆炸药以及一些食物和药品。对我们来说,眼下这些东西简直是雪中送炭,一时间恐惧都被喜悦冲淡了不少。
三炮找了一番还不罢休,忍着恶心将那些人身上也检查了一遍,把戒指、手表、项链之类的也扒拉了下来。
看到我们的表情不自然起来,三炮解释道反正该拿的也拿了,这些东西扔在这儿也只能给南陵王殉葬了,咱本来就是来掀他的斗的,到时候指不定还得撬他的棺材,现在用不着跟他这么客气。
充实了自己的装备后,我们的底气足了不少,总算不至于再那么狼狈了,就算真遇上什么恶鬼粽子,这些家伙足够顶上好一阵子了。人就是很奇怪,有时候手里捧着危险的东西,反而更有安全感。
我们把白得的东西都点了一下,枪械之类的分发,有用的装包带走。鹰戈在那些人的身上也翻了翻,当然他和三炮不一样,不是为求财,这应该是龙少的意思,看看能不能找出些能证明他们身份的东西。一翻果然有点收获,在其中一个人的上衣口袋里,鹰戈摸出了一个笔记本。
这并非笔记本电脑,而是纸质的笔记本,看来这个人有记笔记的习惯。鹰戈把笔记本递给我,我随手翻看了几眼。这个人还有点浪漫主义情调,笔记本首页记的是一首诗,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我愿为激流》,但往后翻翻,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就是一些探险经历和个人感触什么的,和我们经历的都大差不差的。可能这支队伍的保密工作做得比较严格,真正泄露行踪和行动机密的内容是不允许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的。
一看没什么重要内容,我将它递给风师爷,他翻看了两页便觉得没有什么价值,随手将其丢掉,笔记本内页一展,忽然一个东西从里面掉了出来。我定睛一看,居然是一张黑白照片。
之前还真没发现笔记本里还夹着东西,它掉出来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弯腰伸手捡起,拿到眼前细看。
这是一张黑白照片,且有些年头了,但是照片却比较新,相信应该是用底片新洗出来的。照片的背面写着几个字母:AIIH,似乎是一个英语单词,正面是一队人的合影,分四排共三十多人,清一色的英军军服,看起来就像是某个飞行大队在合影。
不过他们不全是大鼻子老外,其中也有东亚人和印度人,只是看不出那几个东亚人究竟是不是中国人。
照片右下角用白色字写着日期:1944年5月13日,应该是照片拍摄的日期,没想到这居然是二战时期的,这照片怎么会在那人的身上?按理说无关的人不会带这样的照片,难道这里面有人是他的祖辈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又扫了一眼那照片,突然,照片中的一张面孔一下刺激了我的眼球,让我猛吸了一口气。我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再一看才证实自己没有看错,与此同时,心中的那种怪异感却越来越强烈了。
照片中最后一排左起第四人,居然和龙少长得一模一样。